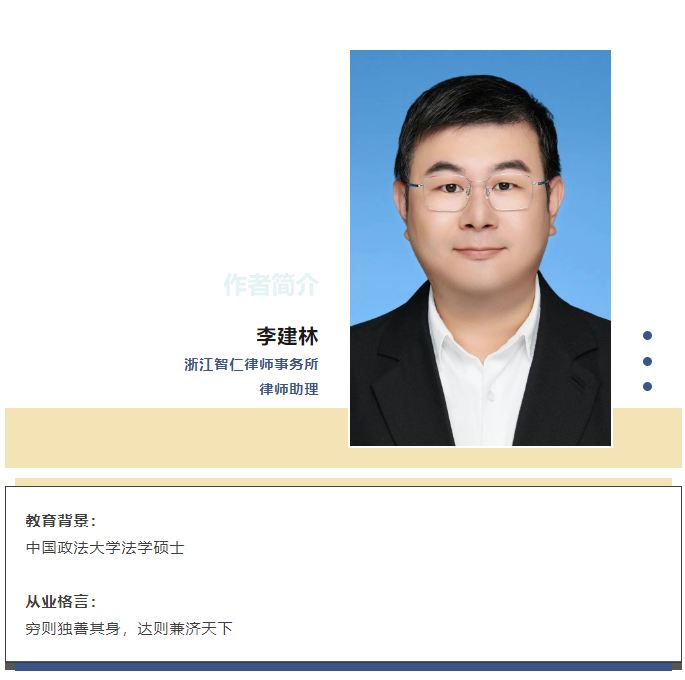|
传闻证据制度之鸟瞰——刑诉法再修改之前思
作者:毛丽英、李建林、王雨寒 近日,相关权威性文章指称,刑事诉讼法修改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迅速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在关于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具体制度和程序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中,提出增加“传闻证据制度”这一证据可采性规则。该制度作为舶来品,肇始于普通法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未明确规定。值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机,作者想借助有关文献,较为浅显、朴素地介绍该制度,由于该制度内容体系庞杂,无法面面俱到,不当之处予以指正。 一、传闻证据制度简介 例:乙向丙转述其目击甲盗窃过程,案件需要查明甲是否实施盗窃。两种情形:(1)乙出庭陈述作证;(2)丙出庭陈述作证。传闻证据制度主要旨在排除丙出庭陈述作证的情形。为何要确立传闻证据制度?概括起来,理由有三: 1.最大限度确保证言可信度。若乙出庭陈述作证该过程,则该证据可信度主要受制于乙自身认识、记忆、表达等能力以及诚信品质;但是若丙出庭陈述作证该过程,概率上可信度将双倍降低,该证据的可信度不仅受到乙自身的影响,同时还会叠加丙的相关因素。 2.无法通过具结(宣誓)、对质、反诘等程序予以验证证言可信度。若乙出庭陈述作证,可以通过具结(宣誓),增强对其证言真实性的内心约束(注:通常经过具结作伪誓,可能涉嫌伪证罪,对于证人产生内心强制力);法庭通过观察其言行,来判断其证言的可信度(注:类似中国古代的“五听”制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对质、反诘问,暴露其证言存在的问题。但若丙陈述作证,上述程序的适用将无法予以保证。 3.陪审团制度的影响。陪审团并非法律专家,容易受到影响,尽量减少陪审团接触到不可靠的传闻证据,通过直接适用该制度,剥夺可信度低的传闻证据的证据资格,避免此类证据进入证据门槛。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传闻证据规则是涉及证据可采性的规则,其本身是判断证据资格的问题。 二、传闻证据制度的适用范围 1.传闻与非传闻的判断。很显然,传闻证据制度针对的证据类型是传闻证据,非传闻证据不适用该制度。传闻的判断需要跟待证事实相结合。以“乙向丙转述其目击甲盗窃过程”为例,若待证事实是“甲是否盗窃”时,即丙的证言即是传闻,因为待证事实与“乙陈述作证内容的真实性”有关;但若待证事实是“乙告知过丙甲盗窃的这一事实”,则丙的证言即“非传闻”,因为待证事实与“乙陈述作证内容的真实性”无关。事实上,对于传闻与非传闻的判定众说纷纭,异常困难。可以用一条思路简要区辨厘清。首先要明确,证据与待证事实有关,对于待证事实结论的得出需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其中在证明“甲盗窃”这个事实中,我们需要亲身感知“甲盗窃”的乙出庭,才能避免上文所述传闻证据可能导致的弊端,因为听从丙的转述,将会受到丙自身因素的影响。但若是证明“乙是否告知丙甲盗窃”这个事实,丙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注:在证明甲盗窃时,丙不是亲历者),所以,尽管也涉及乙的陈述,但此时陈述就跟传闻无关。 2.传闻证据包括传闻证言和目击证言的书面记录。在“乙向丙转述其目击甲盗窃过程”的例子中,丙对于甲盗窃过程非亲历所感,其在法庭内证言,属于传闻证人证言,系传闻证据;乙在庭外对于侦查或者检察机关所为的证言所形成的书面记载,同样也是传闻证据。 三、传闻证据例外规则 传闻证据制度为了尽可能确保证言的可信度而原则上排斥庭外证言(包括传闻证言和目击证言的书面记录),理由在上文中已提到,当然“尽可能确保”只能针对一般情况而非个案(注:庭外证言可信度一定低吗?在个案中并不一定,只能说从整体观察风险比较高),但事实上有些客观情况,目击证人确无法出庭,比如目击证人下落不明、目击证人已去世,若在此种情况下完全排除传闻证据,有时反而会对事实的查明产生影响,必须在确保证言可信度与查明事实之间予以“衡平”。因此域外立法例通过两种模式规定了传闻证据例外规则,在符合例外的情形下,传闻证据具有可采性,取得证据资格。 1.具体列举部分场合下的传闻证据具有可采性,取得证据资格。例如,美国等国家规定的传闻证据制度中,临终证言往往是作为普遍容许的例外。理由在于:目击证人已死,从客观上讲本身已无法出庭作证,若机械遵循传闻证据制度排斥该证言的证据资格,反而导致无法查明事实。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证言受制于客观情况下,通常可信度较高。(注:事实上,临终证言的可信度一定高吗?是否会受到行为人临终状态的意识、表达影响呢?这里所谓的可信度高主要是建立在临终状态下行为人撒谎的可能性降低,因此临终证言从科学上讲是否一定属于例外范畴仍有商讨之处。)证据的“双重危险”(即目击证人的证言可信度和传闻证人转述可信度的风险)相较于一般情形有所降低。因此对于临终证言,就不从证据资格上绝对予以排斥,而是委之以证明力规则,由法官通过内心自由心证予以判断。 2.不具体列举场合,而是通过“可信性”与“必要性”基准粗略判断。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传闻证据制度中,其列举了审判外向法官、侦查中向检察官以及调查中向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所为的陈述的例外。但是对于三者情形同样予以区分:对于审判外向法官的陈述,是概括容许得为证据;对于侦查中向检察官的陈述,一般容许得为证据,但显有不可信时则否定证据资格;对于调查中向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所为的陈述,则一般否定证据资格,在具有必要性或可信性时则例外容许。然而相关实务认为此种处理,不当过大了传闻证据制度例外范围的适用,事实上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从优先保护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角度,对于庭外陈述的容许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已保证被告人对质诘问权”这一程序要件。 四、思考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了增加传闻证据规则的意见,具有重大意义,值此之机,也浅显提出作者不成熟想法。 1.传闻证据制度的定义如何表述,是否需要规定传闻的含义。前文提到,传统意义上传闻证据制度适用对象是传闻证据,不包括非传闻证据。但是传闻证据与非传闻证据的区分确是模糊的,若规定传闻证据制度,是否需要具体描述传闻的定义,还是委之以司法实践予以丰富完善。 2.考虑到长期以来书面证言的普遍化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客观事实,传闻证据的范围尤其是例外容许的范围如何确定。对于庭外证言的例外容许情形,是采取具体描述式(例如临终证言),还是基准式(例如可信性和必要性)。 3.传闻证据制度与配套制度的配合。例如,若是规定了直接言词原则,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被告人对质诘问权以及相关程序保障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