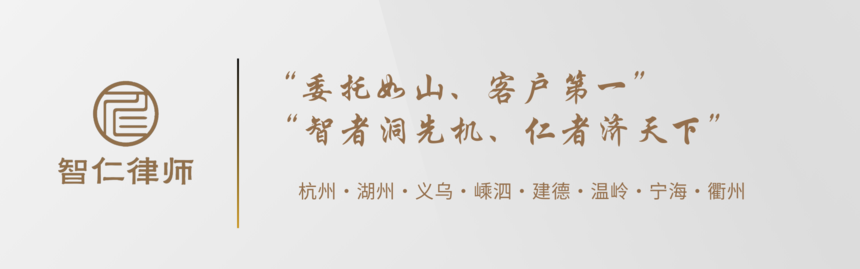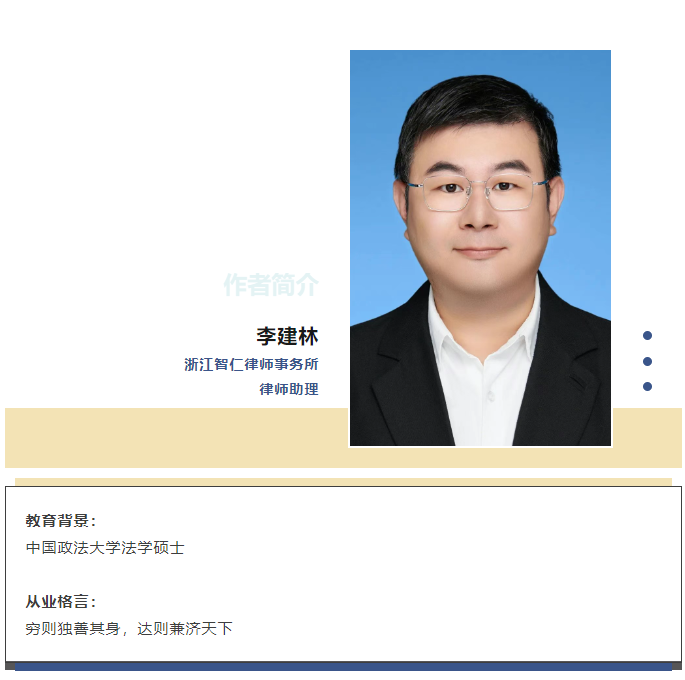|
共犯脱离问题理论与实务研究——刑法理论与实务系列研究(四)
一、共犯脱离的基本理论 (一)共犯脱离的含义 在共同犯罪的场景中,共犯犯罪形态的认定采取“一部行为全体责任”,即“一人着手,全体着手”、“一人既遂、全体既遂”。但是若采取共犯的处罚根据系“惹起说”(注:惹起说是共犯处罚根据的学说之一,是指之所以要处罚共犯,在于其行为引起了构成要件事实的发生。),则当共犯被迫或者自主切断其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因果性时,则共犯不需要在承担既遂责任,而只能论以预备犯、未遂犯或者中止犯。这种因共犯切断构成要件结果因果关联而导致其从共同犯罪中脱离的现象,刑法理论称作“共犯脱离”。举个简单的案例予以说明(改编自王皇玉教授《刑法总则》): 【三人抢劫案】甲系某富豪的司机,意外得知富豪的保险箱密码,并邀请乙、丙一同前往富豪家中抢劫,三人在前往途中,乙心生畏惧,告知甲、丙不想一起犯案,甲、丙同意,后乙离开。 在这则案例中,假设乙只是单纯同意甲的意思前往富豪家中抢劫,而在离开之前既未与甲、丙共谋设计具体的行抢计划或者方案,同时也没有提供钥匙、工具等物理帮助,则若乙明确告知甲、丙自己不想犯案,并且离开,则乙脱离了共同犯罪,由于乙是预备阶段自动脱离,乙可能被论以抢劫罪的中止犯(预备阶段中止)。 (二)共犯脱离的类型及理论学说 根据相关学说,共犯脱离按照时间点区分,包括着手前脱离和着手后脱离;按照共犯类型区分,包括共同正犯脱离和狭义共犯(教唆犯、帮助犯)脱离。 1.着手前的脱离 (1)山口厚教授观点:(参见山口厚著,付立庆译《刑法总论》) 教唆犯:必须要使正犯放弃实施犯罪的意思,或者至少是使正犯一度改变主意。帮助犯:切断物理的因果性以及心理的因果性。就物理的因果性来说,比如取回犯罪道具或者一度使正犯改变主意,就心理的因果性而言,通过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或者只要是正犯认识到了脱离。共同正犯:类似于教唆犯、帮助犯,但在共谋的场合,必须祛除共谋效果。 (2)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 基本与山口厚教授的观点相同,但在帮助犯场合,张明楷教授认为,帮助者要消除物理的因果性,不以通告正犯或共同正犯为前提,只要客观上消除物理的因果性即可;而要消除心理的因果性,则以通告正犯或共同正犯为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3)王皇玉教授的观点:(参见王皇玉《刑法总则》) 王皇玉教授以前述【三人抢劫案】为例,乙在共同实行之前脱离,说明其已不再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固然可以从共同正犯中脱离;然而若乙除前往豪宅行抢的行为外,还有其他参与实行的行为,例如教唆行抢或提供物理性帮助等,若未能切断这些行为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因果性,则其仍有可能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形式参与共同犯罪。 2.着手后的脱离 (1)山口厚教授观点:(参见山口厚著,付立庆译《刑法总论》) 山口厚教授列举了日本相关判例,指出部分判例认为在着手后脱离需要脱离人实施“阻止犯罪继续实行的措施”,并且在部分判例中,无论着手前脱离还是着手后脱离,两者的要件并无不同,都需要满足这一点。 (2)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 有当参与人消除了先前的行为对犯罪结果的促进作用,导致先前的共犯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性时,才属于共犯关系的脱离。 (3)王皇玉教授的观点:(参见王皇玉《刑法总则》) 王皇玉教授认为需要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停止放弃自己的行为;二是表明脱离共同正犯的意思,并使他人明了;三是除去先前所为对于犯罪的影响力,切断因果关系。 总结:从上面的相关学者观点来看,要形成共犯脱离,总体要求是共犯切断自己行为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因果性,但具体采用何种基准判断“切断”,则未形成非常明确的标准,原则上着手脱离前的标准宽松于着手脱离后的标准。 二、共犯脱离的审判实务及分析 (相关案例通过Alpha查询、援引) 案例一 被告人李某某、俞某某等开设赌场案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2018)苏0118刑初364号 法院针对被告人俞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俞某某在共同开设赌场期间有十几天未参与开设赌场,属于共犯脱离”的辩护意见,认为,共犯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既遂之前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而本案开设赌场罪在各被告人共同设立赌场进行赌博之时已经既遂,被告人俞某某即便期间有未参与情形,亦不属于共犯脱离,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案例二 许某某、彭某某、陈某某等诈骗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刑终201号 该案经过两审终审。二审法院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陈某某于2017年6月2日交付的电脑未实际用于临安的诈骗,彭某某脱离了与被告人陈某某等人的共犯关系”的辩护意见,指出共犯的脱离不仅行为人应向其他共同犯罪人明示其退出犯罪,还应积极有效消除之前共犯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彭某某虽然退出公司在临安阶段的诈骗,但其作为本案诈骗发起者之一、公司的大股东,并未有效制止公司搬到临安后的诈骗行为,故应对陈某某等人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全部诈骗活动承担责任。 案例三 冯某某、靳某某故意伤害案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皖01刑终388号 该案法院认为,共同犯罪中共犯脱离犯罪,行为人必须同时消除已经实施的共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物理因果性与心理因果性。冯某某虽口头告知靳某某停止对向某某实施侵害,但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其他共犯继续犯罪,没有切断其对王某某等实行犯心理上的支持,也没有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未能消除其先前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冯某某不成立犯罪中止。 案例四 李某某、许某甲寻衅滋事案 灵宝市人民法院(2018)豫1282刑初381号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人李某某、许某甲、许某乙等人喝酒唱歌后,因被告人李某某酒醉踩到蔡某某的脚,双方发生争执,引起打架。上述被告人对蔡某及其随行的席某某、续某某进行殴打,致蔡某某、席某某、续某某受伤。另法院还查明,被告人许某乙在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过程中,中途离开。 法院认为被告人许某乙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中途离开,但其并未实施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中止,而属于共同犯罪脱离行为,因其在共同犯罪中参与时间较短,故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 简析:从上述四个案例,可以窥见实务观点关于共犯脱离的一些观点。 1.共犯脱离应当在犯罪既遂之前。共犯脱离主要目的在于共犯参与人是否脱离共同犯罪关系,一旦脱离,则该参与人不需要对于脱离后的其他共同参与人导致的构成要件既遂结果承担责任,如果在着手前的脱离,行为人根据脱离的自愿性,可以认定为预备或者中止,而针对着手后的脱离,则根据脱离的自愿性,可以认定为未遂或者中止。在案例一中,开设赌场罪通常被认定为行为犯,不同于结果犯必须具有具体外化结果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一般行为犯只需要行为完成即犯罪既遂。因此若开设赌场罪因为开设赌场的行为已经完成而被认定为犯罪既遂的情况下,共犯即不能脱离共同犯罪关系。 2.共犯脱离的“切断”标准包括“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消除共犯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性”、“阻止其他犯罪参与者继续实行犯罪”。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实务中对于共犯能否脱离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案例二提到“共犯的脱离不仅行为人应向其他共同犯罪人明示其退出犯罪,还应积极有效消除之前共犯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该案例二提到共犯脱离的两个标准指征,一是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同时该意思表示需要明示;二是消除共犯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性。案例三,则提到“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共犯继续犯罪”,则又提出一个新的标准指征。相较于案例二、案例三,案例四中法院对于共犯脱离的标准并未提出如此高的标准,在该案中,许某乙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离开现场,但并未采取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法院认为尽管许某某不构成犯罪中止,但仍属于共犯脱离。 3.共犯脱离的标准还需要审查共犯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案例三中,法院认为,彭某某虽然退出公司在临安阶段的诈骗,但其作为本案诈骗发起者之一、公司的大股东,并未有效制止公司搬到临安后的诈骗行为,故应对陈某某等人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全部诈骗活动承担责任。 4.共犯中止与共犯脱离并非同一问题。实务中有存在将共犯中止的成立要件运用于共犯脱离,事实上,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犯中止是共犯脱离的一种特殊情形,要求行为人自愿防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但共犯脱离则是共犯切断其行为与共犯结果的因果性后,不承担共犯既遂责任。脱离的共犯人并不需要一定自愿,也不要求必须防止共犯结果的发生。当然若成立共犯中止,则必然已经共犯脱离。案例四提到,法院认为被告人许某乙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中途离开,但其并未实施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中止,而属于共同犯罪脱离行为。 三、总结 从上述理论与实务来看,我们对于共犯脱离提出不成熟的观点: 1.共犯脱离的理论实务意义在于解消共犯参与人的共犯关系,使得脱离后的共犯参与人对于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既遂结果不承担责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尽管不构成犯罪中止但的确愿意脱离共同犯罪的共犯参与人,另设从宽处理的另一条路径。 2.共犯脱离,根据其脱离的阶段、自愿性等,在犯罪形态上认定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在教唆犯的场合,原则上由于犯意系教唆犯引起,则教唆犯的脱离,必须有切断其教唆行为导致既遂结果发生的因果性,应当认为只有打消正犯的犯意方才脱离。帮助犯的场合,根据帮助系心理帮助或是物理帮助有所区分,心理帮助若要脱离则要求帮助犯必须使共犯参与人了解其对于犯罪不再提供助力方为脱离,其中既包括明示共犯参与人自己不再参与犯罪,或者以行为标明自己不再参与犯罪。在共同正犯场合,若在着手前,原则按照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脱离处理,通常需要明示或者以行动标明自己脱离共同犯罪,然而在参与共谋的情况下,除非打消其他共犯参与人实施共谋计划而另外落实犯罪计划,否则不能脱离;在着手后,除需要采取上述脱离措施外,关键在于避免其他共犯人利用其脱离后的残余贡献,因此着手后的脱离通常需要避免其他共犯人继续实行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